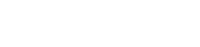第三十六章 继位
后半夜,风停了。
战场上的血腥味还没散尽,可厮杀声已经彻底消失。士兵们沉默地清理着战场,将一具具尸首抬上马车,运往远处的荒原。火把的光芒在夜色里跳动,照亮那些沾满血污的脸,也照亮那把空荡荡的王座。
短短一日,一席汗位,换了三人。
士兵清理完战场,趁着夜色回了云州。几千骑兵离去时悄无声息,转眼便消失在茫茫夜色里。只留下满地的血迹,证明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阿尔德站在营地中央,召集了那些躲过一劫的颉利发旧部。
“颉利发已死。”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全场,“你们是他的部属,我不勉强。愿意留下的,可以并入阿史那部,一视同仁。不愿意的,可以带着你们的家人和牲畜,去投奔其他部落。”
那些旧部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这场叛乱竟然就这样结束了。
没有清算,没有追杀,没有斩草除根。
就这样……让他们走?
有人试探着问:“二王子……不,可汗,您真的放我们走?”
阿尔德看着他:“我说过的话,从不收回。”
那人愣了片刻,忽然跪下去,额头抵着地面:“我愿留下,愿为新可汗效犬马之劳!”
有一就有二。那些旧部纷纷跪下,七嘴八舌地表着忠心。也有少数几个犹豫着,最终带着家人悄然离去。阿尔德没有拦,只是看着他们消失在夜色里。
牧民们听见外面安静了,渐渐从帐篷里探出头来。
一个,两个,十个,百个。
很快,营地里又站满了人。
诺敏从帐篷里出来时,脸上的震惊还没褪去。她看着阿尔德,看着满地的血迹,半晌说不出话。
雅娜尔站在她身边,倒是拍手称快。
“杀得好!”她看着颉利发倒下的方向,眼里闪着快意的光,“这种畜生,死一万次都不够。”
柳望舒站在人群边缘,看着这一切。
她看着阿尔德站在高处,看着众人渐渐聚拢过来,看着那些目光从惊恐变成敬畏,从怀疑变成臣服。
卡姆颤巍巍地走出来。
她看着阿尔德,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她举起那枚狼头金印,还沾着血迹。
“继位仪式,继续。”她的声音苍老却清晰,“长生天在上,阿史那部的血脉不绝,可汗之位,不可一日空悬。”
她走到阿尔德面前,将那枚金印举过头顶。
“阿史那·阿尔德,战功赫赫,品行端方。今日,在金帐之前,在部众眼前,你,可愿接过这枚金印,成为阿史那部新的可汗?”
阿尔德看着那枚金印。
金印上沾着巴尔特的血,也沾着颉利发的血。那是他血脉至亲的血,也是他亲手斩断的羁绊。
他伸出手,接过金印。
“我愿意。”
萨满的鼓声再次响起。这一次,没有惊慌失措的逃窜,没有刀光剑影的厮杀。只有沉沉的鼓声,一下一下,像心跳,像这片土地千百年来不变的脉搏。
众人跪下。
“可汗——!”
“可汗——!”
“可汗——!”
呼声如潮水,一波一波,涌向那个站在高处的人。
阿尔德站在王座前,俯视着脚下跪倒的人群。
他终于,成为了这片草原的新主人。
——
第二日,金帐内,阿尔德坐在那把还带着血腥气的位置上,面前摊着羊皮纸和笔墨。
帐帘掀开,三位阏氏都走了进来。
她们都在他对面坐下,等着他开口。
阿尔德没有抬头,只是看着面前的羊皮纸,像在斟酌什么。
草原上有两条法则:一是胜者拥有一切,二是可汗过世,其所有妻子(除生母外),皆属新汗。
柳望舒是知道的,她的手指微微收紧。她已经将诺敏和雅娜尔的情况提前给阿尔德讲过了,但她还是紧张。
阿尔德抬起头,看着诺敏:“诺敏。”他开口,“你在部落里操持内务,辛苦多年。若想回回纥去,什么时候想回来看看,都可以。”
“雅娜尔。”他继续道,“你这些年……辛苦了,回契丹和阙特勤团聚吧。”
诺敏倒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即使她心里已十分满意这个结果。
只是雅娜尔,她愣愣地阿尔德说完,半晌没有动。
“你说什么?”她的声音发颤,“你……放我走?”
“是。”阿尔德没有抬眼,继续翻阅着手里的文书,“我会派人护送你到契丹那边。”
雅娜尔捂住嘴,眼泪夺眶而出。
她猛地站起身抱住柳望舒。
“阿依!”雅娜尔抱着她,又哭又笑,像个疯了的女人,她知道肯定是柳望舒在其中帮了忙,“阿依,谢谢你!谢谢你!”
柳望舒被她勒得有些喘不过气,却没有推开。
她轻轻拍着雅娜尔的背。
“去吧。”柳望舒轻声说,“去找他。”
雅娜尔松开她,眼睛红红的,脸上却满是笑意。她用力点头,然后转身,大步往自己的帐篷跑去。
“阿依!”她的声音从帐外传来,“你也要好好的!”
柳望舒笑着点头。
诺敏也告退。
阿尔德的声音传来:“那你呢?”
柳望舒抬头看着汗位上的阿尔德。
他已经站起身,看着她:“你为她们做好了打算,你的呢?”
“你也要回长安吗?”他问,声音很轻,拳头却攥紧了,紧张,忐忑,像等待宣判的人。
柳望舒看着他紧绷的下颌,攥紧的拳头,看着他那双深静的眼睛里,那一点藏不住的、怕失去的害怕。
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站在戈壁的月光下,递给她酒袋。
她想起诺鲁孜节的篝火旁,他唱那首《心爱的姑娘》。
她想起他一次次送来婴儿用的东西,想起他站在她的帐篷前,久久不肯离去。
她想起那晚意乱情迷的瞬间……
还有他说的那些话。
她忽然笑了。
“你……”她轻声问,“希望我回吗?”
阿尔德没有说话,径直朝她走来。
他的身形高大,在她面前站定时,将她完全笼罩在阴影里。她需要仰起头,才能看清他的脸。
他伸出手,握住她的双臂,握得很紧,紧得她有些疼。
“柳望舒。”他唤她,声音低哑,像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
这是第一次,他用这个名字唤她,不是作为阏氏,不是作为公主,只是作为她自己。
“你……”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像是在鼓起全部的勇气,“可以留在我身边吗?”
柳望舒抬头看着他认真的眼神。
他继续道,一字一顿,像是怕她听不清:“留在这里,做我唯一的阏氏,可以吗?”
唯一的阏氏。
不是之一,是唯一。
十年了。
从她十六岁到二十六岁,从少女到妇人。
他一直都在她身边。
她的眼眶忽然湿了。
眼泪滑落下来,无声无息。
她点了点头。
阿尔德的眼睛亮了。
他松开她的双臂,俯身轻轻吻去她脸上的泪。很轻,很柔,像月光落在水面上。没有欲望,只有珍重,和压抑了太久太久、终于可以释放的温柔。
“我要给你最盛大的婚礼。”他低声说,“让整个草原都知道,你属于我。”
后半夜,风停了。
战场上的血腥味还没散尽,可厮杀声已经彻底消失。士兵们沉默地清理着战场,将一具具尸首抬上马车,运往远处的荒原。火把的光芒在夜色里跳动,照亮那些沾满血污的脸,也照亮那把空荡荡的王座。
短短一日,一席汗位,换了三人。
士兵清理完战场,趁着夜色回了云州。几千骑兵离去时悄无声息,转眼便消失在茫茫夜色里。只留下满地的血迹,证明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阿尔德站在营地中央,召集了那些躲过一劫的颉利发旧部。
“颉利发已死。”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全场,“你们是他的部属,我不勉强。愿意留下的,可以并入阿史那部,一视同仁。不愿意的,可以带着你们的家人和牲畜,去投奔其他部落。”
那些旧部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这场叛乱竟然就这样结束了。
没有清算,没有追杀,没有斩草除根。
就这样……让他们走?
有人试探着问:“二王子……不,可汗,您真的放我们走?”
阿尔德看着他:“我说过的话,从不收回。”
那人愣了片刻,忽然跪下去,额头抵着地面:“我愿留下,愿为新可汗效犬马之劳!”
有一就有二。那些旧部纷纷跪下,七嘴八舌地表着忠心。也有少数几个犹豫着,最终带着家人悄然离去。阿尔德没有拦,只是看着他们消失在夜色里。
牧民们听见外面安静了,渐渐从帐篷里探出头来。
一个,两个,十个,百个。
很快,营地里又站满了人。
诺敏从帐篷里出来时,脸上的震惊还没褪去。她看着阿尔德,看着满地的血迹,半晌说不出话。
雅娜尔站在她身边,倒是拍手称快。
“杀得好!”她看着颉利发倒下的方向,眼里闪着快意的光,“这种畜生,死一万次都不够。”
柳望舒站在人群边缘,看着这一切。
她看着阿尔德站在高处,看着众人渐渐聚拢过来,看着那些目光从惊恐变成敬畏,从怀疑变成臣服。
卡姆颤巍巍地走出来。
她看着阿尔德,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她举起那枚狼头金印,还沾着血迹。
“继位仪式,继续。”她的声音苍老却清晰,“长生天在上,阿史那部的血脉不绝,可汗之位,不可一日空悬。”
她走到阿尔德面前,将那枚金印举过头顶。
“阿史那·阿尔德,战功赫赫,品行端方。今日,在金帐之前,在部众眼前,你,可愿接过这枚金印,成为阿史那部新的可汗?”
阿尔德看着那枚金印。
金印上沾着巴尔特的血,也沾着颉利发的血。那是他血脉至亲的血,也是他亲手斩断的羁绊。
他伸出手,接过金印。
“我愿意。”
萨满的鼓声再次响起。这一次,没有惊慌失措的逃窜,没有刀光剑影的厮杀。只有沉沉的鼓声,一下一下,像心跳,像这片土地千百年来不变的脉搏。
众人跪下。
“可汗——!”
“可汗——!”
“可汗——!”
呼声如潮水,一波一波,涌向那个站在高处的人。
阿尔德站在王座前,俯视着脚下跪倒的人群。
他终于,成为了这片草原的新主人。
——
第二日,金帐内,阿尔德坐在那把还带着血腥气的位置上,面前摊着羊皮纸和笔墨。
帐帘掀开,三位阏氏都走了进来。
她们都在他对面坐下,等着他开口。
阿尔德没有抬头,只是看着面前的羊皮纸,像在斟酌什么。
草原上有两条法则:一是胜者拥有一切,二是可汗过世,其所有妻子(除生母外),皆属新汗。
柳望舒是知道的,她的手指微微收紧。她已经将诺敏和雅娜尔的情况提前给阿尔德讲过了,但她还是紧张。
阿尔德抬起头,看着诺敏:“诺敏。”他开口,“你在部落里操持内务,辛苦多年。若想回回纥去,什么时候想回来看看,都可以。”
“雅娜尔。”他继续道,“你这些年……辛苦了,回契丹和阙特勤团聚吧。”
诺敏倒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即使她心里已十分满意这个结果。
只是雅娜尔,她愣愣地阿尔德说完,半晌没有动。
“你说什么?”她的声音发颤,“你……放我走?”
“是。”阿尔德没有抬眼,继续翻阅着手里的文书,“我会派人护送你到契丹那边。”
雅娜尔捂住嘴,眼泪夺眶而出。
她猛地站起身抱住柳望舒。
“阿依!”雅娜尔抱着她,又哭又笑,像个疯了的女人,她知道肯定是柳望舒在其中帮了忙,“阿依,谢谢你!谢谢你!”
柳望舒被她勒得有些喘不过气,却没有推开。
她轻轻拍着雅娜尔的背。
“去吧。”柳望舒轻声说,“去找他。”
雅娜尔松开她,眼睛红红的,脸上却满是笑意。她用力点头,然后转身,大步往自己的帐篷跑去。
“阿依!”她的声音从帐外传来,“你也要好好的!”
柳望舒笑着点头。
诺敏也告退。
阿尔德的声音传来:“那你呢?”
柳望舒抬头看着汗位上的阿尔德。
他已经站起身,看着她:“你为她们做好了打算,你的呢?”
“你也要回长安吗?”他问,声音很轻,拳头却攥紧了,紧张,忐忑,像等待宣判的人。
柳望舒看着他紧绷的下颌,攥紧的拳头,看着他那双深静的眼睛里,那一点藏不住的、怕失去的害怕。
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站在戈壁的月光下,递给她酒袋。
她想起诺鲁孜节的篝火旁,他唱那首《心爱的姑娘》。
她想起他一次次送来婴儿用的东西,想起他站在她的帐篷前,久久不肯离去。
她想起那晚意乱情迷的瞬间……
还有他说的那些话。
她忽然笑了。
“你……”她轻声问,“希望我回吗?”
阿尔德没有说话,径直朝她走来。
他的身形高大,在她面前站定时,将她完全笼罩在阴影里。她需要仰起头,才能看清他的脸。
他伸出手,握住她的双臂,握得很紧,紧得她有些疼。
“柳望舒。”他唤她,声音低哑,像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
这是第一次,他用这个名字唤她,不是作为阏氏,不是作为公主,只是作为她自己。
“你……”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像是在鼓起全部的勇气,“可以留在我身边吗?”
柳望舒抬头看着他认真的眼神。
他继续道,一字一顿,像是怕她听不清:“留在这里,做我唯一的阏氏,可以吗?”
唯一的阏氏。
不是之一,是唯一。
十年了。
从她十六岁到二十六岁,从少女到妇人。
他一直都在她身边。
她的眼眶忽然湿了。
眼泪滑落下来,无声无息。
她点了点头。
阿尔德的眼睛亮了。
他松开她的双臂,俯身轻轻吻去她脸上的泪。很轻,很柔,像月光落在水面上。没有欲望,只有珍重,和压抑了太久太久、终于可以释放的温柔。
“我要给你最盛大的婚礼。”他低声说,“让整个草原都知道,你属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