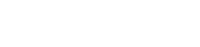安稚鱼不懂自己的眼眶为什么睁得更圆了一些,里面迅速积聚起滚烫的湿意,像是被火烤着。
她嗫嚅着唇瓣,不懂为什么要向安霜解释,要向安暮棠狡辩,“我没有。”
她轻飘飘地吐出这三个字,如同金鱼在水中吐泡一般,然后转过头低下。
安霜回过身,她知道一段感情不是无故产生的,三十天的□□纠缠背后,是长达六年的相濡以沫与惺惺相惜。这个认知像冰冷的潮水漫过胸腔,带来灭顶的窒息感。
“怪不得……怪不得你们这几天的相处这么古怪。”她的声音带着疲惫与难以置信的颤抖,“你们不觉得恶心吗?你们还记不记得自己姓什么?记不记得你们叫的是同一个母亲!还知不知道你们是姐妹!”
她的音量再次拔高,锐利的目光直刺安暮棠:“安暮棠,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收场?啊?是打算就这么偷偷摸摸一辈子,还是玩腻了就把你妹妹一脚踹开?你恶劣不恶劣啊!”
“妈妈,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你应该问妹妹。”
“你说什么?”
安暮棠扭头,目光沉沉地落在安稚鱼身上,“关系主导权从来就不在我这儿,不是我想怎样就怎样。”
“少给我来这套诡辩!”
安霜的怒火再次被点燃,她逼近安稚鱼,声音压得更低,却更令人心慌,“你之前闹着要解除领养关系,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能名正言顺地跟你姐姐在一起吗?”
安稚鱼一愣,随即摇头:“不是,和她没有半分关系!我只是觉得我的人生规划,应该和安家的每一个人都割裂开。对于这点,我很抱歉。”
这是她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此刻却显得如此苍白。
“你发誓。”安霜盯着她,脸色苍白得吓人,让安稚鱼瞬间想起她并不稳定的健康状况。
几乎没有犹豫,安稚鱼抬起一只手,大拇指用力按住小指,将剩余三根手指笔直地竖起的姿态带着一种决绝的意味:“我发誓——”
话音未落,一只微凉的手猛地擒住了她的手腕,力道之大,让她感到骨骼生疼。安稚鱼顺着力道看去,安暮棠修长的手指紧紧箍着她,那枚戴在她指间的素圈戒指,在灯光下反射出碎光。
安稚鱼眸光一暗,没忍住蜷缩了手指,随后甩开了安暮棠的禁锢。
安暮棠的话一字一句钻进她耳朵里,“你的人生规划里没有我吗。”
安稚鱼下意识反问,“难不成你的就有我了吗。”
“你没问过我,你也不信我。”
耳边是茶杯炸碎开的尖锐叫音,安霜几乎是气得胸口剧烈起伏。
她忍无可忍,上前扇了安暮棠一巴掌,“事到如今你还没觉得自己错吗。其他的我也不想知道了,我就想知道你们谁先开启的这个头?”
“我。”安暮棠捂着半边被扇的脸,那巴掌足以给她脸上染上一层红,看上去倒是有几分认错的态度,只不过话说得铿锵有力,丝毫不怕再落下一巴掌。
“是我先引诱她的。”
安稚鱼摇头,抓着安霜发颤的手,“不是这样的……是我一直缠着她,求她给我收拾烂摊子,求她——”
“在我范围之内,我不愿意的事没人能让我去做。”安暮棠一牵动嘴角,撕裂般的麻木感就涌上来,仿佛在提醒她闭嘴,抱着自己高高在上的自尊心一同安静下来。
“是我主动给你的手机安装追踪器,因为我不准你的行程对我有分毫隐瞒,是我主动提出成为你唯一的绘画缪斯,因为我不准你的画笔,勾勒出除我之外的任何身影,是我主动去那个小镇找你,因为我怕你在祭拜完生母后,会产生任何我不能接受的的念头……安稚鱼,如果我不愿意,你那所谓的‘七天胁迫’,根本不会开始。”
她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砸在安稚鱼的心上,也砸在安霜的认知里。
“我处心积虑,在你过去的每一寸光阴里塞满我的痕迹,让你只能依靠我的呼吸存活。”她凝视着安稚鱼,眼中翻涌着复杂难言的情绪,是偏执,是痛楚,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求,“结果你现在告诉我,你规划的未来里没有我?”
这些迟来的东西,过了表达的时机,如同屋檐下初凝的冰凌,早已失去了水的柔韧,只剩下冰冷的坚硬和迟来的刺痛。虽然本质一样,但又不一样。
安霜已经在一旁惊得难以说话,她看不出来自己优秀寡言的大女儿揣着这些腌臜的心思。
“够了!我不是来听你们的诉衷肠的!我现在要给赵今仪打电话,我要问问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有些踉跄地拿起手机,深吸一口气,对安稚鱼说,“你先回房睡觉,把门关好。所有事,明天再说。”
睡觉?经历了这样兵荒马乱、心脏几经碾碎的一晚,谁还能安然入睡?
安稚鱼整个人都是懵的,像被抽空了灵魂的木偶。
她机械地后退两步,意识到自己无法在这个令人窒息的空间里多待一秒。她可以接受明天的审判,但绝不能在此刻假装无事发生。
她转身冲回房间,很快又出来,身上已经换了一套可以出门的便服,手里紧紧攥着手机。
“抱歉,我不留在这里了,给你们添麻烦,我以后不会再出现你们面前。”
安霜看着她,沉默了很久,久到空气都再次凝固。最终,她疲惫地闭上眼,再睁开时,里面只剩一片荒凉。
“解除领养关系的事,不用等到我死了。你想什么时候办,联系我。到时候你想当天上的鸟,还是水里的鱼,都没人能管你了。”
安稚鱼愣住了。她没想到,最终的“惩罚”竟是这样一种近乎放弃的“成全”。这或许是安霜看在过往情分上,对她最后的仁慈。而这仁慈,比责骂更让她感到无地自容。
她喉咙哽咽,一句话也说不出。忽然,她走到安霜面前,屈膝,弯腰,额头重重磕在柔软的地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这是一个充满愧悔与诀别意味的举动。
这个动作,彻底刺激到了原本还能维持一丝镇定的安暮棠。
她猛地意识到,这一磕头,或许就要将安稚鱼从此磕出她的生命。她还想动作,但长时间跪坐让她的双腿麻木僵硬,刚一试图起身,就险些栽倒。她只能下意识地伸手,紧紧抓住近在咫尺的安霜的手臂,借着这点支撑,才勉强摇摇晃晃地站直身体。
“妈……”她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无法抑制的慌乱和哭腔,泪水毫无预兆地滚落,迅速染红了眼眶,“你让她别走,我和她之间的事,还没有说完,还没有解决,你说过的事情要有始有终。”
安霜想抽回手臂,却被她抓得更紧,看着大女儿泪流满面、摇摇欲坠的样子,终究没忍心用力推开。
“安暮棠!你还不明白吗?”安霜痛心疾首,早已顾不得什么优雅仪态,“她是个聪明人!她知道什么该取,什么不该取!你醒一醒!”
“不是这样的,我了解她,她不是……”安暮棠用力摇头,泪水更加汹涌,清澈的眼白布满血丝,那总是清冷自持的面具碎裂殆尽,露出底下近乎绝望的脆弱。
“我从小想要的,你们都不给我,为什么现在还是不行……”
她的哭声越来越大,软化了原本清晰的吐字,将那最后一点倔强的自尊也融化在模糊不清的哽咽里。那未尽的话语,被汹涌的泪水淹没,只剩下无边无际的悲伤与不甘,在惨白的灯光下无声蔓延。
oooooooo
作者留言:
姐姐好不容易勇敢一次,发现妹妹因为大脑宕机而不跟自己统一战线,破防ing 另外,其实我的大纲是he来着……[彩虹屁]
第39章
安稚鱼跌跌撞撞走到楼下, 一看时间,已经是夜半一点,街道空旷, 只有几盏孤独的路灯投下昏黄的光晕, 将她的影子拉扯得变形、瘦长。
她搜了一下附近, 有几家好评较多的酒店,环境相对安全, 于是挑了最近一家入住。
房间位于十二楼,比她想象中还要静谧。双层隔音玻璃仿佛一道无形的屏障, 将楼下城市隐约的喧嚣彻底过滤, 连偶尔驶过的车辆鸣笛声,都变成了遥远、沉闷的嗡鸣。
安静是好事, 但对于安稚鱼来说同样也是一件坏事。
这过分的安静, 反而成了回忆最好的扩音器。那些她拼命想要压制的画面和声音, 争先恐后地在她脑海中清晰起来。
仿佛安暮棠对她做的那些事,说的那些话还发生在眼前, 她总是很讨厌回想少年时期的事情, 因为那些提醒着自己,大胆却愚蠢,安暮棠不喜欢她,厌恶她, 简直是避恐不及。
但是安暮棠却说, 她是故意的, 她是刻意让自己沦陷的。
安稚鱼仰倒在床上, 眼泪从眼角缓缓掉下去, 隐没在发丝中。她明明已经扭头朝着另一条平坦的路走了, 可是转身又发现之前那条荆棘路没了尖刺, 反而生长出了一簇一簇的花。
她嗫嚅着唇瓣,不懂为什么要向安霜解释,要向安暮棠狡辩,“我没有。”
她轻飘飘地吐出这三个字,如同金鱼在水中吐泡一般,然后转过头低下。
安霜回过身,她知道一段感情不是无故产生的,三十天的□□纠缠背后,是长达六年的相濡以沫与惺惺相惜。这个认知像冰冷的潮水漫过胸腔,带来灭顶的窒息感。
“怪不得……怪不得你们这几天的相处这么古怪。”她的声音带着疲惫与难以置信的颤抖,“你们不觉得恶心吗?你们还记不记得自己姓什么?记不记得你们叫的是同一个母亲!还知不知道你们是姐妹!”
她的音量再次拔高,锐利的目光直刺安暮棠:“安暮棠,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收场?啊?是打算就这么偷偷摸摸一辈子,还是玩腻了就把你妹妹一脚踹开?你恶劣不恶劣啊!”
“妈妈,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你应该问妹妹。”
“你说什么?”
安暮棠扭头,目光沉沉地落在安稚鱼身上,“关系主导权从来就不在我这儿,不是我想怎样就怎样。”
“少给我来这套诡辩!”
安霜的怒火再次被点燃,她逼近安稚鱼,声音压得更低,却更令人心慌,“你之前闹着要解除领养关系,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能名正言顺地跟你姐姐在一起吗?”
安稚鱼一愣,随即摇头:“不是,和她没有半分关系!我只是觉得我的人生规划,应该和安家的每一个人都割裂开。对于这点,我很抱歉。”
这是她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此刻却显得如此苍白。
“你发誓。”安霜盯着她,脸色苍白得吓人,让安稚鱼瞬间想起她并不稳定的健康状况。
几乎没有犹豫,安稚鱼抬起一只手,大拇指用力按住小指,将剩余三根手指笔直地竖起的姿态带着一种决绝的意味:“我发誓——”
话音未落,一只微凉的手猛地擒住了她的手腕,力道之大,让她感到骨骼生疼。安稚鱼顺着力道看去,安暮棠修长的手指紧紧箍着她,那枚戴在她指间的素圈戒指,在灯光下反射出碎光。
安稚鱼眸光一暗,没忍住蜷缩了手指,随后甩开了安暮棠的禁锢。
安暮棠的话一字一句钻进她耳朵里,“你的人生规划里没有我吗。”
安稚鱼下意识反问,“难不成你的就有我了吗。”
“你没问过我,你也不信我。”
耳边是茶杯炸碎开的尖锐叫音,安霜几乎是气得胸口剧烈起伏。
她忍无可忍,上前扇了安暮棠一巴掌,“事到如今你还没觉得自己错吗。其他的我也不想知道了,我就想知道你们谁先开启的这个头?”
“我。”安暮棠捂着半边被扇的脸,那巴掌足以给她脸上染上一层红,看上去倒是有几分认错的态度,只不过话说得铿锵有力,丝毫不怕再落下一巴掌。
“是我先引诱她的。”
安稚鱼摇头,抓着安霜发颤的手,“不是这样的……是我一直缠着她,求她给我收拾烂摊子,求她——”
“在我范围之内,我不愿意的事没人能让我去做。”安暮棠一牵动嘴角,撕裂般的麻木感就涌上来,仿佛在提醒她闭嘴,抱着自己高高在上的自尊心一同安静下来。
“是我主动给你的手机安装追踪器,因为我不准你的行程对我有分毫隐瞒,是我主动提出成为你唯一的绘画缪斯,因为我不准你的画笔,勾勒出除我之外的任何身影,是我主动去那个小镇找你,因为我怕你在祭拜完生母后,会产生任何我不能接受的的念头……安稚鱼,如果我不愿意,你那所谓的‘七天胁迫’,根本不会开始。”
她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砸在安稚鱼的心上,也砸在安霜的认知里。
“我处心积虑,在你过去的每一寸光阴里塞满我的痕迹,让你只能依靠我的呼吸存活。”她凝视着安稚鱼,眼中翻涌着复杂难言的情绪,是偏执,是痛楚,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求,“结果你现在告诉我,你规划的未来里没有我?”
这些迟来的东西,过了表达的时机,如同屋檐下初凝的冰凌,早已失去了水的柔韧,只剩下冰冷的坚硬和迟来的刺痛。虽然本质一样,但又不一样。
安霜已经在一旁惊得难以说话,她看不出来自己优秀寡言的大女儿揣着这些腌臜的心思。
“够了!我不是来听你们的诉衷肠的!我现在要给赵今仪打电话,我要问问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有些踉跄地拿起手机,深吸一口气,对安稚鱼说,“你先回房睡觉,把门关好。所有事,明天再说。”
睡觉?经历了这样兵荒马乱、心脏几经碾碎的一晚,谁还能安然入睡?
安稚鱼整个人都是懵的,像被抽空了灵魂的木偶。
她机械地后退两步,意识到自己无法在这个令人窒息的空间里多待一秒。她可以接受明天的审判,但绝不能在此刻假装无事发生。
她转身冲回房间,很快又出来,身上已经换了一套可以出门的便服,手里紧紧攥着手机。
“抱歉,我不留在这里了,给你们添麻烦,我以后不会再出现你们面前。”
安霜看着她,沉默了很久,久到空气都再次凝固。最终,她疲惫地闭上眼,再睁开时,里面只剩一片荒凉。
“解除领养关系的事,不用等到我死了。你想什么时候办,联系我。到时候你想当天上的鸟,还是水里的鱼,都没人能管你了。”
安稚鱼愣住了。她没想到,最终的“惩罚”竟是这样一种近乎放弃的“成全”。这或许是安霜看在过往情分上,对她最后的仁慈。而这仁慈,比责骂更让她感到无地自容。
她喉咙哽咽,一句话也说不出。忽然,她走到安霜面前,屈膝,弯腰,额头重重磕在柔软的地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这是一个充满愧悔与诀别意味的举动。
这个动作,彻底刺激到了原本还能维持一丝镇定的安暮棠。
她猛地意识到,这一磕头,或许就要将安稚鱼从此磕出她的生命。她还想动作,但长时间跪坐让她的双腿麻木僵硬,刚一试图起身,就险些栽倒。她只能下意识地伸手,紧紧抓住近在咫尺的安霜的手臂,借着这点支撑,才勉强摇摇晃晃地站直身体。
“妈……”她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无法抑制的慌乱和哭腔,泪水毫无预兆地滚落,迅速染红了眼眶,“你让她别走,我和她之间的事,还没有说完,还没有解决,你说过的事情要有始有终。”
安霜想抽回手臂,却被她抓得更紧,看着大女儿泪流满面、摇摇欲坠的样子,终究没忍心用力推开。
“安暮棠!你还不明白吗?”安霜痛心疾首,早已顾不得什么优雅仪态,“她是个聪明人!她知道什么该取,什么不该取!你醒一醒!”
“不是这样的,我了解她,她不是……”安暮棠用力摇头,泪水更加汹涌,清澈的眼白布满血丝,那总是清冷自持的面具碎裂殆尽,露出底下近乎绝望的脆弱。
“我从小想要的,你们都不给我,为什么现在还是不行……”
她的哭声越来越大,软化了原本清晰的吐字,将那最后一点倔强的自尊也融化在模糊不清的哽咽里。那未尽的话语,被汹涌的泪水淹没,只剩下无边无际的悲伤与不甘,在惨白的灯光下无声蔓延。
oooooooo
作者留言:
姐姐好不容易勇敢一次,发现妹妹因为大脑宕机而不跟自己统一战线,破防ing 另外,其实我的大纲是he来着……[彩虹屁]
第39章
安稚鱼跌跌撞撞走到楼下, 一看时间,已经是夜半一点,街道空旷, 只有几盏孤独的路灯投下昏黄的光晕, 将她的影子拉扯得变形、瘦长。
她搜了一下附近, 有几家好评较多的酒店,环境相对安全, 于是挑了最近一家入住。
房间位于十二楼,比她想象中还要静谧。双层隔音玻璃仿佛一道无形的屏障, 将楼下城市隐约的喧嚣彻底过滤, 连偶尔驶过的车辆鸣笛声,都变成了遥远、沉闷的嗡鸣。
安静是好事, 但对于安稚鱼来说同样也是一件坏事。
这过分的安静, 反而成了回忆最好的扩音器。那些她拼命想要压制的画面和声音, 争先恐后地在她脑海中清晰起来。
仿佛安暮棠对她做的那些事,说的那些话还发生在眼前, 她总是很讨厌回想少年时期的事情, 因为那些提醒着自己,大胆却愚蠢,安暮棠不喜欢她,厌恶她, 简直是避恐不及。
但是安暮棠却说, 她是故意的, 她是刻意让自己沦陷的。
安稚鱼仰倒在床上, 眼泪从眼角缓缓掉下去, 隐没在发丝中。她明明已经扭头朝着另一条平坦的路走了, 可是转身又发现之前那条荆棘路没了尖刺, 反而生长出了一簇一簇的花。